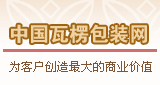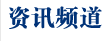從浙江到廣東,從河南到四川……飽受爭議的中國鉛酸蓄電池產業正經歷一次前所未有的休克式療法。
力度最大的當屬浙江。浙江蓄電池行業協會秘書長姚令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目前浙江省273家鉛蓄電池企業,已有近250家被關停,關停比例高達92%。關停者中,不乏天能、超威、南都電源等上市公司的下屬企業。
用在汽車、摩托車的啟動電池和電動自行車上的鉛酸蓄電池,因鉛污染難消等原因,一直遭受口誅筆伐。2010年國內發生的6起較大鉛污染事件中,一半由鉛酸蓄電池企業引起。而在浙江,今年不到半年之內,更連出臺州與德清海久電池兩起血鉛事件。
鉛酸蓄電池企業整治,因此被作為2011年環保專項行動的首要任務。環保部、工信部等九部委2011年4月開始這項行動,要求全面徹查鉛酸蓄電池企業環境違法問題。
一個月后,5月18日,環保部再度發出通知,要求“加強鉛蓄電池及再生鉛行業污染防治工作”,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要確保污染物穩定達標排放、落實500米的衛生防護距離、建立重金屬污染責任終身追究制。“整頓已事關整個行業的生死存亡。”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副理事長王敬忠說。正因如此,數周來,蓄電池行業的游說工作已全面發動,中國電池工業協會、中國電器工業協會鉛酸蓄電池分會等紛紛出動。
交戰“500米”
游說的重點“在于衛生部的500米防護距離標準”。王敬忠說,中國有95%至99%的企業都達不到這標準。衛生防護距離是指產生有害因素的部門的邊界至居住區邊界的最小距離。
事實上,制定于1989年的這條“500米”標準,在環保部門的環評中長期遭到忽略。曾陪環保部官員多次視察鉛酸電池企業的蓄電池專家、蘇州大學教授王金良說,2008年前建廠的企業,大多數環評的衛生防護距離并未被嚴格要求。在行業協會看來,1989年防護距離標準制定時,國內的鉛酸蓄電池仍多以手工為主,規模小、技術低、污染嚴重在所難免。目前時過境遷,這一標準恐有待商榷。
此外,許多企業在建廠之初,尚處城郊,多年過去后,規劃中的居民區漸漸“包圍工廠”,最終讓許多企業“被動”地不符要求而遭停產。這樣的調整,“讓企業承擔全部責任也不是很合理”。
王金良透露,此前衛生部也曾打算修改早前的防護距離。2009年,他受托主持制定這一防護距離標準的修改。通過一系列測定、測算,最終確定為300米的方案,但報到國家標準化委員會后,“不知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批準”。
更令浙江企業頗有微詞的是,在九部委統一行動下,各省市采取的措施并不一致,“廣東、天津執行的是300米的標準,而浙江就一直要求嚴格執行防護距離,難免會予人不公平的感覺。”一位要求匿名的知名鉛酸蓄電池企業董事長說。
超威集團董事長周明明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希望能請專家組織專業團隊進行整體再評估。經過完整、系統、專項的檢測評估后,再確定一個距離,不管最終結果是更遠還是更近,都會更科學一些。
對于整改工作,周明明建議應分兩步來走:一方面最好有個過渡的時間;其次,行業在一定時間內、達到什么樣的標準,最好能盡快量化。“企業就按照這個目標去做,做不到就關停”。
當整頓遭遇游擊隊
鉛酸電池行業的整治一直在進行。2005年前后,浙江長興等地曾爆發多起血鉛群體事件,一度引發政府鐵腕治理。之后,中國更在鉛酸蓄電池行業實行生產許可證制度,對于新開辦的企業實行嚴格審批制度。“但糟糕的是,很多作坊式的小企業更像是游擊隊。”王敬忠說,這邊關停了,這些企業又換個地方重新開張。
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對外公布的數字顯示,我國有2000多家鉛酸蓄電池企業,有生產許可證的企業約1800家,產值在500萬元以上的企業只有200多家,不到整體數量的10%,而產值在億元以上的更少。
一幢居民樓,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工廠,七八個人,買來電池的材料手工組裝。這樣作坊式的小企業,在蓄電池廠商中并不罕見。“根本沒有環保設備,基本采取手工或半手工操作方式。”“門檻低、分布散、規模小、水平低,整個行業一直飽受詬病。”5月31日,王敬忠如此概括中國鉛酸電池行業的現狀。
鉛酸蓄電池專家、蘇州大學教授王金良說,鉛酸蓄電池產業的污染主要來自兩個環節:生產與回收,其中再生鉛的回收污染則比電池生產更為惡劣。由于小作坊多為露天熬制,揮發后四溢的鉛煙,冶煉后隨處丟棄的鉛渣。小工廠在回收電池過程中,把酸液直接傾倒,酸液所到之處,寸草不生。“這樣的小企業,沒有現代的生產工藝,產品質量沒有保證,污染行為沒有約束,對整個行業負面影響很大。”王敬忠說。
長興當地一名地方官員坦承,游擊隊式的小作坊并不少見。長興蓄電池占國內45%左右市場份額,2004年長興“500兒童血鉛中毒”事件后,蓄電池這一“支柱產業”遭受重創——許多小企業被清理關停。
不過,轉眼間,這些企業便成為安徽、江西等欠發達地區招商的香餑餑。
與長興接壤的安徽廣德縣一名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證實,廣德一度成為長興落后電池企業的接收地。雖然條件不符,但依然有數十家涉鉛企業涌入縣內,其中更有24家取得合法手續。落后的工藝很快引發了環境危機,直至2008年原廣德縣委書記鄒河要求全面關停,才告一段落。
有意無意的環境監管不力也成為污染事件的推手。多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蓄電池企業大多無法達到環保要求,但許多地方政府出于經濟利益考慮,依然讓他們通過了環評。“更糟糕的是,許多引進的企業中還有當地干部的干股。”
社會穩定亦在考慮之中。知情人士則說,在企業大規模停產的“蓄電池之鄉”長興,政府已派干部下鄉維護停產企業的穩定,并給部分企業員工發放每月300元的補貼。
環保不投,血鉛難除
整治能否逼迫企業進行環保投入?至少現在來看,鉛酸蓄電池產業的環保投入頗巨,非一般小企業所能承擔。
王金良介紹,目前工廠每生產一萬千伏安時蓄電池的環保運行費用大約需要3萬到6萬元,而其銷售收入不過五六百萬,利潤率很低,大多數企業凈利潤只有3%,最高也不會超過5%。
“產值幾千萬,拿出幾千萬投資,還要每年上千萬的維護費用,怎么可能?”王敬忠說。也因此,國內企業的環保設備投入和運行積極性普遍不高。
“只有規模化企業才能承擔得起巨額的環保投入。”王金良說。美國鉛酸蓄電池產量跟中國差不多,但卻只有33家電池廠。在良好的管理下,美國鉛酸蓄電池產業還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長,在蓄電池里也占到61%份額。
“根本的問題不在于防護距離,而應對環境進行嚴格的評價。”王金良說,以他了解的美國江森自控公司為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鉛酸蓄電池公司,江森旗下的鉛酸蓄電池企業,環保設施做得很好,有無衛生防護距離并無太大區別。
“他們車間生產過程中產生的鉛粉塵,幾乎全被9臺除塵器吸收重新利用。單除塵這一項,一年電費開支近千萬元。”一位曾參觀過長興引進的美國江森公司項目的電池企業老總感慨說,該項目僅用于環保設備的一次性投入就達到1000萬美元,僅此一筆,在國內就可再投資多個規模生產企業。
準入門檻正在重新制定。王敬忠透露,中國電池工業協會已配合工信部起草了廢舊鉛酸電池回收處理行業的準入條件。新建廠年處理能力要達5萬噸以上,老廠也要達到2萬噸,“達不到一律淘汰”,初步設想是最終保留二三十家回收企業,最后向社會公布資質。
鉛酸蓄電池生產企業的準入條件也在起草之中。草案從規模和環保設計方面提出更高門檻以阻止落后企業進入,“老廠要在20萬千伏安時規模以上,新建的也在年50萬千伏安時規模以上”。達到如此生產規模,產值達8000萬以上到一個億,才有能力投入環保設備。“通過整頓來進行產業整合與提升”或許是中國蓄電池管理部門的現實做法。王敬忠說,在當下的國民經濟中,鉛酸蓄電池擁有廣泛的使用領域,舉足輕重。它涉及國防、電動自行車、輕型電動汽車、太陽能風能儲能電池等諸多領域,僅以電動自動車為例,其保有量就達1.5億輛。
但更關鍵的是,如王金良所說,由于“鉛酸電池性價比更高、性能更穩定、更安全,加上鉛的回收率已達到98.5%”,當下鉛酸蓄電池依然無法被新生的鋰電池替代。“既然這個行業必須繼續存在,我們更多考慮的就應是怎么來幫助它發展、規范它,而不是抹殺它。”天能集團董事張天任說。
調整或已開始。2011年5月30日,姚令春參加了由浙江省環保廳召開的聯席會議,討論的正是行業整治后的驗收標準問題。
 評論表單加載中...
評論表單加載中...